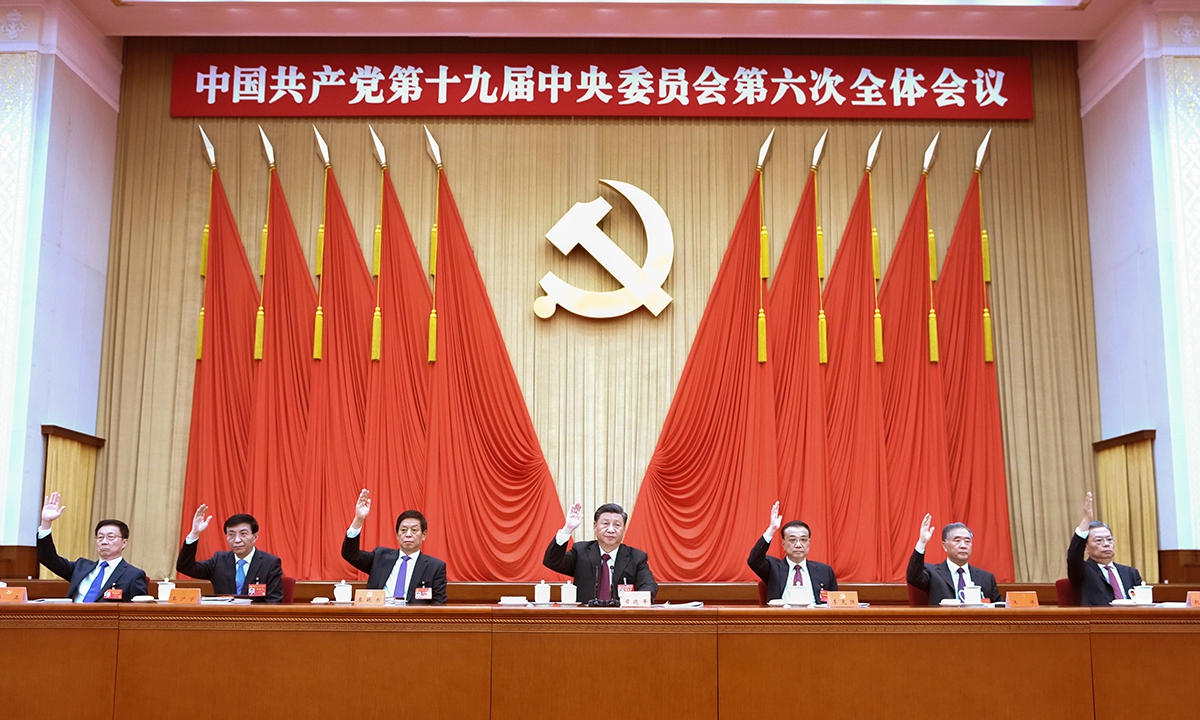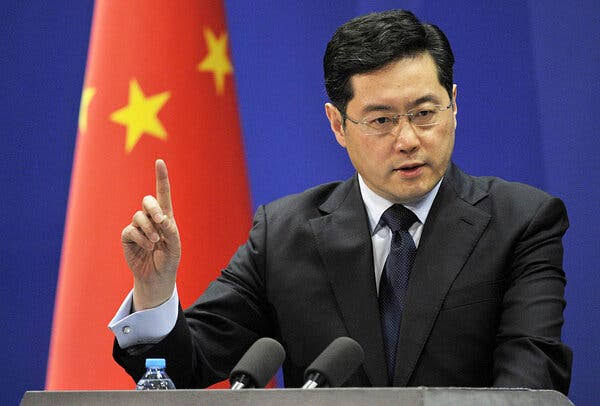еңЁдёӯеӣҪе№ҝиўӨзҡ„еҶңжқ‘еӨ§ең°дёҠпјҢиҖҒйҫ„еҢ–е’ҢзӨҫдјҡдҝқйҡңзјәдҪҚжӯЈдәӨз»ҮжҲҗдёҖйҒ“йҡҫд»ҘеӣһйҒҝзҡ„зҺ°е®һеӣҫжҷҜгҖӮеңЁжҹҗдәӣеҒҸиҝңең°еҢәпјҢиҖҒдәәйқ зқҖжҜҸе№ҙеҮ еҚғе…ғзҡ„е…»иҖҒйҮ‘еӢүеҠӣз»ҙз”ҹпјҢжңүзҡ„иҝҳиҰҒеңЁе…«еҚҒеІҒй«ҳйҫ„ж—¶жӢ…иө·дҝқе®үзҡ„е·ҘдҪңпјҢд»ҘиЎҘиҙҙ家用гҖӮеңЁеӯҗеҘіеҠӣдёҚд»ҺеҝғгҖҒеҢ»з–—иҙ№з”Ёй«ҳжҳӮзҡ„иғҢжҷҜдёӢпјҢдёҖдәӣиҖҒдәәжңҖз»ҲйҖүжӢ©дәҶжңҖжһҒз«Ҝзҡ„ж–№ејҸз»Ҳз»“з—ӣиӢҰгҖӮ
дёҖдҪҚеҶңжқ‘иҖҒдәәзҡ„ж—ҘеёёиҙҰжң¬
еңЁж№–еҢ—жҹҗдёӘеҶңдёҡе’ҢеҢ–е·Ҙ并йҮҚзҡ„е°Ҹй•ҮпјҢдёҖдҪҚиҝ‘е…«ж—¬зҡ„иҖҒдәәдҫқж—§еқҡжҢҒе·ҘдҪңпјҢжҜҸеӨ©еңЁеҢ–иӮҘеҺӮй—ЁеҸЈзңӢе®ҲеӨ§й—ЁгҖӮд»–дёҖе№ҙзҡ„е…»иҖҒйҮ‘еҸӘжңү1800е…ғпјҢеҚҙиҰҒж”Ҝд»ҳеҢ»дҝқгҖҒж°ҙз”өзӯүејҖй”ҖпјҢеҮ д№ҺжүҖеү©ж— еҮ гҖӮиҝҷд»Ҫдҝқе®үе·ҘдҪңиҷҪ然е·Ҙиө„дёҚй«ҳпјҢеҚҙжҳҜд»–иө–д»Ҙз»ҙз”ҹзҡ„ж №жң¬вҖ”вҖ”йҷӨдәҶжҳҘиҠӮпјҢд»–е…Ёе№ҙж— дј‘пјҢдёҖдәәеқҡе®ҲеІ—дҪҚгҖӮ
иҝҷж ·зҡ„еІ—дҪҚжқҘд№ӢдёҚжҳ“гҖӮдёҠдёҖд»Ҫе·ҘдҪңзҡ„еҢ–е·ҘеҺӮеӣ з–«жғ…еҒңдә§пјҢиҖҒжқҝиҮӘжқҖпјҢе‘ҳе·ҘеӨұдёҡгҖӮд»–еҜ№жӣҫз»Ҹзҡ„е·ҘдҪңеҚ•дҪҚдҫқ然еҝғжҖҖж„ҹжҝҖпјҢе“ӘжҖ•еҪ“е№ҙзҡ„е·Ҙиө„дҪҺдәҺжңҖдҪҺж ҮеҮҶпјҢжҜ«ж— зҰҸеҲ©гҖӮ
еҹҺд№Ўе…»иҖҒйҮ‘е·®и·қеҰӮйёҝжІҹ
иҝҷдҪҚиҖҒдәәзҡ„еўғеҶө并йқһдёӘдҫӢгҖӮеңЁд»–зҡ„жқ‘еә„пјҢй«ҳйҫ„д»Қе·ҘдҪңиҖ…жҜ”жҜ”зҡҶжҳҜгҖӮз»ҹи®Ўж•°жҚ®жҳҫзӨәпјҢеҶңжқ‘иҖҒдәә收е…ҘдёӯпјҢд»…42.7%жқҘиҮӘе…»иҖҒйҮ‘е’ҢеҢ»дҝқзӯүзҰҸеҲ©пјҢи¶…иҝҮдёүжҲҗеҲҷйңҖйқ дҪ“еҠӣеҠіеҠЁз»ҙжҢҒгҖӮиҖҢеңЁеҹҺеёӮпјҢзү№еҲ«жҳҜдҪ“еҲ¶еҶ…йҖҖдј‘дәәе‘ҳдёӯпјҢе…»иҖҒйҮ‘еҸҜиҫҫе…ӯеҚғе…ғз”ҡиҮіжӣҙеӨҡгҖӮ
иҝҷз§ҚжӮ¬ж®ҠиғҢеҗҺпјҢжҳҜеҶңжқ‘е…»иҖҒдҪ“зі»зҡ„и„ҶејұгҖӮеңЁи®ЎеҲ’з»ҸжөҺи§ЈдҪ“еҗҺпјҢеҶңжқ‘д»ҺйӣҶдҪ“з»ҸжөҺиҪ¬дёәдёӘдҪ“жүҝеҢ…пјҢзҰҸеҲ©еҲ¶еәҰйҡҸд№Ӣз“Ұи§ЈгҖӮеӨҡж•°иҖҒдәәеҸӘиғҪйўҶеҸ–жңҖдҪҺжЎЈж¬Ўзҡ„е…»иҖҒйҮ‘пјҢд»…еӨҹз»ҙжҢҒеҹәжң¬з”ҹжҙ»гҖӮ
еҶңжқ‘еңҹең°зҡ„з§ҹйҮ‘иҷҪдҪҺпјҢеҚҙеҜ№е№ҙиҝҲиҖ…иҖҢиЁҖе·ІжҳҜи§Ји„ұгҖӮи®ёеӨҡиҖҒдәәе°Ҷеңҹең°иҪ¬еҢ…пјҢд»…дҝқз•ҷдёҖеқ—иҸңең°иҮӘз»ҷиҮӘи¶ігҖӮйҖўе№ҙиҝҮиҠӮпјҢжүҚиҲҚеҫ—еҗғдёҖж¬ЎиӮүгҖӮ
еҢ»з–—ж”ҜеҮәеҰӮеұұеҺӢйЎ¶
еҢ»з–—жҳҜеҶңжқ‘иҖҒдәәжңҖж— жі•жүҝеҸ—д№ӢйҮҚгҖӮж №жҚ®з»ҹи®ЎпјҢеҶңжқ‘иҖҒдәәдҪҸйҷўиҮӘиҙ№йғЁеҲҶе№іеқҮи¶…иҝҮ8000е…ғпјҢеҮ д№ҺзӯүдәҺ他们全е№ҙзҡ„收е…ҘгҖӮж–°еҶңеҗҲиҷҪ然жҸҗдҫӣдәҶдёҖе®ҡзҡ„еҢ»дҝқжҠҘй”ҖпјҢдҪҶиҰҶзӣ–иҢғеӣҙгҖҒжҠҘй”ҖжҜ”дҫӢе’ҢжҠҘй”Җйҷҗйўқжҷ®йҒҚеҒҸдҪҺпјҢе°Өе…¶жҳҜй—ЁиҜҠиҙ№з”ЁпјҢеӨ§еӨҡйңҖиҮӘиҙ№гҖӮ
ж…ўжҖ§з—…жҲҗдёәвҖңж…ўжҖ§ејҖй”ҖвҖқгҖӮдёҖдҪҚе№ҙйҖҫеҸӨзЁҖзҡ„еҶңжқ‘еҘіжҖ§пјҢиҷҪеҸ—иҝҮж•ҷиӮІпјҢеҚҙеӣ й«ҳиЎҖеҺӢгҖҒзі–е°ҝз—…еёёе№ҙйңҖжңҚиҚҜпјҢжҜҸжңҲиҚҜиҙ№иҮӘиҙҹдёҠеҚғе…ғпјҢе…Ёе№ҙжҠҘй”ҖйўқеәҰж—©ж—©з”Ёе°ҪгҖӮеҘ№жӣҫйқ еңЁеҹҺеёӮж‘Ҷж‘ҠгҖҒе°Ҹжң¬з»ҸиҗҘз§Ҝж”’дёӢеҮ еҚҒдёҮе…ғз§Ҝи“„пјҢеҚҙеңЁиҝ”д№Ўе…»иҖҒеҗҺиҝ…йҖҹиҖ—е°ҪгҖӮ
еҘ№зҡ„家еәӯдёҚж„ҝеҜ№ж”ҝеәңеӨҡеҠ жҢҮиҙЈгҖӮеңЁеҶңжқ‘пјҢж”ҝеәңеҫҖеҫҖжҳҜдёҖдёӘе‘Ҫд»Өзҡ„еӯҳеңЁпјҢиҖҒдёҖиҫҲдәәеҜ№ж”ҝзӯ–зҗҶи§ЈжңүйҷҗпјҢд№ҹе°ұж— жі•жҸҗеҮәжү№иҜ„жҲ–дәүеҸ–жӣҙеӨҡжқғзӣҠгҖӮз—…з—ӣдёҺиҙ«з©·пјҢйғҪиў«и§ҶдёәвҖңе‘ҪвҖқпјҢе”ҜжңүеҝҚиҖҗгҖӮ
еӯҗеҘіжңүеҝғж— еҠӣпјҢе…»иҖҒйҮҚжӢ…ж— еӨ„е®үж”ҫ
еңЁдј з»ҹи§ӮеҝөдёӯпјҢе…»е„ҝйҳІиҖҒжҳҜеҶңжқ‘зҡ„ж ёеҝғдҝЎд»°гҖӮ然иҖҢпјҢзҺ°е®һдёӯзҡ„еҶңжқ‘йқ’е№ҙеӨҡдёәиҝӣеҹҺеҠЎе·Ҙдәәе‘ҳпјҢеңЁеҹҺеёӮдёӯжү“жӢјжң¬е°ұиү°йҡҫпјҢеҶҚеҠ дёҠеӯҗеҘіж•ҷиӮІгҖҒжҲҝиҙ·ејҖй”ҖпјҢе·Іж— еҠӣжүҝжӢ…зҲ¶жҜҚзҡ„й«ҳйўқе…»иҖҒжҲ–еҢ»з–—ж”ҜеҮәгҖӮ
жңүдәӣдёӯиҖҒе№ҙеҘіжҖ§дёәз…§йЎҫеӯҷиҫҲиҖҢиҝӣеҹҺпјҢз”ҡиҮіжҲҗдёәж— еҒҝвҖңдҝқе§ҶвҖқгҖӮдёҖдҪҚжҜҚдәІиҫһиҒҢз…§йЎҫеӯҷеӯҗдёҖе№ҙеҗҺпјҢеӣ ж— ж”¶е…ҘиҖҢз„Ұиҷ‘пјҢжңҖз»ҲйҮҚж–°еӣһеҺӮжү“е·ҘпјҢ并ж”Ҝд»ҳдәІе®¶жҜҚе·Ҙиө„жқҘжӣҝеҘ№з…§ж–ҷеӯҷеӯҗгҖӮеҘ№иҜҙпјҡвҖң没收е…ҘпјҢжҜ”д»Җд№ҲйғҪдёҚиёҸе®һгҖӮвҖқ
иҖҢдёҖдәӣе№ҙиҝҲд»ҚеңЁе·Ҙең°жү“е·Ҙзҡ„вҖңиҖҒе°Ҹе·ҘвҖқпјҢеӨҡж•°жІЎжңүеҠіеҠЁеҗҲеҗҢпјҢй•ҝжңҹж— дҝқйҡңгҖӮеҸ—дјӨж— иө”еҒҝгҖҒеӨұдёҡж— иЎҘеҠ©пјҢе·Ҙең°жёёиө°жҲҗдәҶ他们з”ҹе‘Ҫзҡ„еёёжҖҒгҖӮ
зӨҫдјҡж”ҜжҢҒзҪ‘з»ңзҡ„иЈӮз—•дёҺйҹ§жҖ§
е°Ҫз®ЎеҶңжқ‘иҖҒдәәйқўдёҙйҮҚйҮҚеҺӢеҠӣпјҢ他们д»ҚиҜ•еӣҫжһ„е»әдә’еҠ©ејҸзҡ„е…»иҖҒзҪ‘з»ңвҖ”вҖ”е·ҰйӮ»еҸіиҲҚзӣёдә’з…§еә”пјҢи°Ғ家жңүдәӢеё®дёҖжҠҠпјҢи°Ғз”ҹз—…дәҶдј дёӘиҜқгҖӮдҪҶиҝҷеҘ—зҪ‘з»ңж— жі•жӣҝд»Јдё“дёҡзҡ„еҢ»з–—е’Ңй•ҝжңҹз…§жҠӨжңҚеҠЎгҖӮ
д№ҹжңүеӯҗеҘіз»ҷ家дёӯиЈ…ж‘„еғҸеӨҙиҝңзЁӢзӣ‘жҺ§пјҢдҪҶдәӢж•…д»ҚйҳІдёҚиғңйҳІгҖӮжӣҫжңүдёҖдҪҚй«ҳйҫ„иҖҒдәәж·ұеӨңи·ҢеҖ’пјҢзӣҙеҲ°еӨ©дә®жүҚиў«еҸ‘зҺ°пјҢжңҖз»ҲдёҚжІ»гҖӮиҝҷзұ»дәӢ件并дёҚзҪ•и§ҒгҖӮ
дёҖдёӘеӣҪ家пјҢеҰӮдҪ•и®©иҖҒеҺ»еҸҳеҫ—дҪ“йқўпјҹ
еңЁиҖҒйҫ„еҢ–иҝ…йҖҹеҲ°жқҘзҡ„д»ҠеӨ©пјҢж—Ҙжң¬гҖҒйҹ©еӣҪйғҪеңЁз§ҜжһҒжҺўзҙўе…»иҖҒи§ЈеҶіж–№жЎҲпјҡеҰӮзӨҫеҢәеҢ»з–—дёҺжҠӨзҗҶз»“еҗҲгҖҒе…»иҖҒйҮ‘жҷ®еҸҠдёҺ家еәӯз…§жҠӨз»“еҗҲгҖӮиҖҢдёӯеӣҪзҡ„еҶңжқ‘е…»иҖҒд»Қд»ҘвҖңиҮӘеҠӣжӣҙз”ҹвҖқдёәдё»пјҢеҲ¶еәҰж”ҜжҢҒжңүйҷҗгҖӮ
иҝҷе…¶дёӯдёҚеҸӘжҳҜиө„жәҗй…ҚзҪ®й—®йўҳпјҢд№ҹзүөж¶үеҲ°е…¬е…ұж”ҝзӯ–еҜ№еҶңжқ‘зҡ„й•ҝе№ҙеҝҪи§ҶгҖӮеңЁеҹәеұӮжңҚеҠЎдёҘйҮҚдёҚи¶ігҖҒзҰҸеҲ©еҲ¶еәҰзјәдҪҚзҡ„иғҢжҷҜдёӢпјҢиҖҒдәә们дёҚеҫ—дёҚд»ҘеҠіеҠЁгҖҒдәІжғ…е’ҢйӮ»йҮҢзҪ‘з»ңпјҢиӢҰиӢҰж”Ҝж’‘зқҖиҮӘе·ұзҡ„жҷҡе№ҙгҖӮ
еҪ“ж”ҝзӯ–еҲ¶е®ҡиҖ…й«ҳдёҫвҖңд№Ўжқ‘жҢҜе…ҙвҖқд№Ӣж——пјҢжҳҜеҗҰд№ҹиғҪеҗ¬и§Ғжқ‘еҸЈиҖҒдәәзҡ„еҸ№жҒҜпјҹдёҖдёӘзңҹжӯЈжңүжё©еәҰзҡ„зӨҫдјҡпјҢеә”и®©жҜҸдёҖдҪҚиҖҒдәәпјҢйғҪдёҚеҝ…дёәдёҖйЎҝйҘӯгҖҒдёҖд»ҪиҚҜпјҢе’ҢдёҖдёӘжҳҺеӨ©жӢ…жғҠеҸ—жҖ•гҖӮ

Author: дёӯеӣҪж–°й—»зј–иҫ‘ Charlie
ж¬ўиҝҺйҳ…иҜ»ж–°иҘҝе…°е…ЁжҗңзҙўдёӯеӣҪж–°й—»пјҢжҲ‘们дёәжӮЁеёҰжқҘжңҖж–°зҡ„дёӯеӣҪж–°й—»пјҢи®©жӮЁж—¶еҲ»зҙ§и·ҹдёӯеӣҪзҡ„еҠЁжҖҒдёҺеҸ‘еұ•гҖӮ
вҖ»ж–°иҘҝе…°е…ЁжҗңзҙўВ©пёҸзүҲжқғжүҖжңү
敬иҜ·е…іжіЁж–°иҘҝе…°е…ЁжҗңзҙўNew Zealand Review еңЁеҗ„еӨ§зӨҫдәӨеӘ’дҪ“е№іеҸ°зҡ„е…¬дј—еҸ·гҖӮд»ҺиҝҷйҮҢиҜ»жҮӮж–°иҘҝе…°пјҒпёҸ

ж¬ўиҝҺйҳ…иҜ»ж–°иҘҝе…°е…ЁжҗңзҙўдёӯеӣҪж–°й—»пјҢжҲ‘们дёәжӮЁеёҰжқҘжңҖж–°зҡ„дёӯеӣҪж–°й—»пјҢи®©жӮЁж—¶еҲ»зҙ§и·ҹдёӯеӣҪзҡ„еҠЁжҖҒдёҺеҸ‘еұ•гҖӮ
- дёӯеӣҪж–°й—»зј–иҫ‘ Charlie
- дёӯеӣҪж–°й—»зј–иҫ‘ Charlie
- дёӯеӣҪж–°й—»зј–иҫ‘ Charlie
- дёӯеӣҪж–°й—»зј–иҫ‘ Charlie
- дёӯеӣҪж–°й—»зј–иҫ‘ Charlie
- дёӯеӣҪж–°й—»зј–иҫ‘ Charlie
- дёӯеӣҪж–°й—»зј–иҫ‘ Charlie
- дёӯеӣҪж–°й—»зј–иҫ‘ Charlie
- дёӯеӣҪж–°й—»зј–иҫ‘ Charlie
- дёӯеӣҪж–°й—»зј–иҫ‘ Charlie
- дёӯеӣҪж–°й—»зј–иҫ‘ Charlie
- дёӯеӣҪж–°й—»зј–иҫ‘ Charlie
- дёӯеӣҪж–°й—»зј–иҫ‘ Charlie
- дёӯеӣҪж–°й—»зј–иҫ‘ Charlie
- дёӯеӣҪж–°й—»зј–иҫ‘ Charlie
- дёӯеӣҪж–°й—»зј–иҫ‘ Charlie
- дёӯеӣҪж–°й—»зј–иҫ‘ Charlie
- дёӯеӣҪж–°й—»зј–иҫ‘ Charlie
- дёӯеӣҪж–°й—»зј–иҫ‘ Charlie
- дёӯеӣҪж–°й—»зј–иҫ‘ Charlie
- дёӯеӣҪж–°й—»зј–иҫ‘ Charlie
- дёӯеӣҪж–°й—»зј–иҫ‘ Charlie
- дёӯеӣҪж–°й—»зј–иҫ‘ Charlie
- дёӯеӣҪж–°й—»зј–иҫ‘ Charlie
- дёӯеӣҪж–°й—»зј–иҫ‘ Charlie
- дёӯеӣҪж–°й—»зј–иҫ‘ Charlie
- дёӯеӣҪж–°й—»зј–иҫ‘ Charlie
- дёӯеӣҪж–°й—»зј–иҫ‘ Charlie
- дёӯеӣҪж–°й—»зј–иҫ‘ Charlie
- дёӯеӣҪж–°й—»зј–иҫ‘ Charlie
- дёӯеӣҪж–°й—»зј–иҫ‘ Charlie
- дёӯеӣҪж–°й—»зј–иҫ‘ Charlie
- дёӯеӣҪж–°й—»зј–иҫ‘ Charlie
- дёӯеӣҪж–°й—»зј–иҫ‘ Charlie
- дёӯеӣҪж–°й—»зј–иҫ‘ Charlie
- дёӯеӣҪж–°й—»зј–иҫ‘ Charlie
- дёӯеӣҪж–°й—»зј–иҫ‘ Charlie
- дёӯеӣҪж–°й—»зј–иҫ‘ Charlie
- дёӯеӣҪж–°й—»зј–иҫ‘ Charlie
- дёӯеӣҪж–°й—»зј–иҫ‘ Charlie
- дёӯеӣҪж–°й—»зј–иҫ‘ Charlie
- дёӯеӣҪж–°й—»зј–иҫ‘ Charlie
- дёӯеӣҪж–°й—»зј–иҫ‘ Charlie
- дёӯеӣҪж–°й—»зј–иҫ‘ Charlie
- дёӯеӣҪж–°й—»зј–иҫ‘ Charlie
- дёӯеӣҪж–°й—»зј–иҫ‘ Charlie
- дёӯеӣҪж–°й—»зј–иҫ‘ Charlie
- дёӯеӣҪж–°й—»зј–иҫ‘ Charlie
- дёӯеӣҪж–°й—»зј–иҫ‘ Charlie
- дёӯеӣҪж–°й—»зј–иҫ‘ Charlie
- дёӯеӣҪж–°й—»зј–иҫ‘ Charlie
- дёӯеӣҪж–°й—»зј–иҫ‘ Charlie
- дёӯеӣҪж–°й—»зј–иҫ‘ Charlie
- дёӯеӣҪж–°й—»зј–иҫ‘ Charlie
- дёӯеӣҪж–°й—»зј–иҫ‘ Charlie
- дёӯеӣҪж–°й—»зј–иҫ‘ Charlie
- дёӯеӣҪж–°й—»зј–иҫ‘ Charlie
- дёӯеӣҪж–°й—»зј–иҫ‘ Charlie
- дёӯеӣҪж–°й—»зј–иҫ‘ Charlie
- дёӯеӣҪж–°й—»зј–иҫ‘ Charlie
- дёӯеӣҪж–°й—»зј–иҫ‘ Charlie
- дёӯеӣҪж–°й—»зј–иҫ‘ Charlie
- дёӯеӣҪж–°й—»зј–иҫ‘ Charlie
- дёӯеӣҪж–°й—»зј–иҫ‘ Charlie
- дёӯеӣҪж–°й—»зј–иҫ‘ Charlie
- дёӯеӣҪж–°й—»зј–иҫ‘ Charlie
- дёӯеӣҪж–°й—»зј–иҫ‘ Charlie
- дёӯеӣҪж–°й—»зј–иҫ‘ Charlie
- дёӯеӣҪж–°й—»зј–иҫ‘ Charlie
- дёӯеӣҪж–°й—»зј–иҫ‘ Charlie
- дёӯеӣҪж–°й—»зј–иҫ‘ Charlie
- дёӯеӣҪж–°й—»зј–иҫ‘ Charlie
- дёӯеӣҪж–°й—»зј–иҫ‘ Charlie
- дёӯеӣҪж–°й—»зј–иҫ‘ Charlie
- дёӯеӣҪж–°й—»зј–иҫ‘ Charlie
- дёӯеӣҪж–°й—»зј–иҫ‘ Charlie
- дёӯеӣҪж–°й—»зј–иҫ‘ Charlie
- дёӯеӣҪж–°й—»зј–иҫ‘ Charlie
- дёӯеӣҪж–°й—»зј–иҫ‘ Charlie
- дёӯеӣҪж–°й—»зј–иҫ‘ Charlie
- дёӯеӣҪж–°й—»зј–иҫ‘ Charlie
- дёӯеӣҪж–°й—»зј–иҫ‘ Charlie
- дёӯеӣҪж–°й—»зј–иҫ‘ Charlie
- дёӯеӣҪж–°й—»зј–иҫ‘ Charlie
зӣёе…і
дәҶи§Ј ж–°иҘҝе…°е…Ёжҗңзҙўрҹ”Қ зҡ„жӣҙеӨҡдҝЎжҒҜ
и®ўйҳ…еҗҺеҚіеҸҜйҖҡиҝҮз”өеӯҗйӮ®д»¶ж”¶еҲ°жңҖж–°ж–Үз« гҖӮ